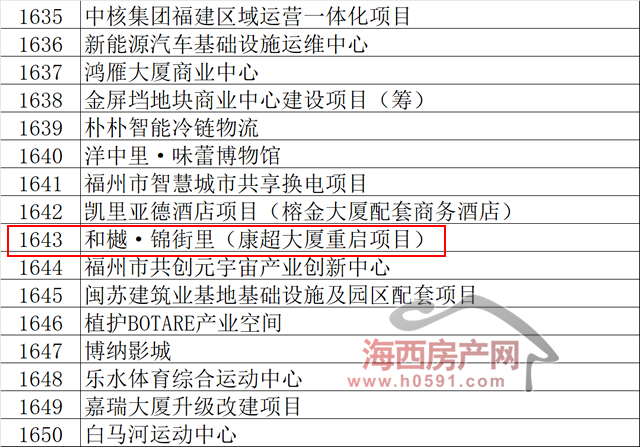在大力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背景下,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社会关系的急剧调整,商品经济的发展打破了传统乡土社会的封闭格局,造就了传统因素和现代因素的并存和对抗,而这种对抗必然会表现为纠纷和冲突的大量出现;与此同时,国家权力的收缩以及自治力量的薄弱也使得基层农村的社会控制能力变得孱弱。农村民事纠纷的解决机制问题开始进入人们关注的视野。在本文中,笔者拟从农村纠纷类型、纠纷解决主体、纠纷解决路径三个方面入手,就这一问题进行初步的剖析,以期从中寻找和发现良方来助力当下的农村民事纠纷解决。
伴随着中国经济社会转型的深入,这种趋势也逐步渗透到乡村地带。在这样一种格局下,原有的价值共识在弱化,利益冲突在加剧,社区分化在加强,乡土社会的秩序受到了很大的冲击,农村纠纷类型在传统与新型生。
(一)传统型农村纠纷,即传统乡土社会历来就有的纠纷类型,具体表现为婚姻家庭纠纷、邻里纠纷、赔偿纠纷、丧葬纠纷、宅基地纠纷、山林土地纠纷等。此种纠纷一般是在农村系统内部,个体之间在日常的生活、劳作中发生的纠纷。传统型农村纠纷强烈的地缘性特征意味着这种纠纷本身暗含了相应的地方性知识以及村落文化的内容,而含量的多少会直接影响到纠纷解决方式的选择,因为含量越高就要求解纷主体对这种地方性知识以及村落文化的通晓程度也要更高,否则纠纷的解决就难以达到理想的效果。
(二)新型农村纠纷,即在转型时期涌现的先前没有出现或者极少出现的农村纠纷,具体表现为合同纠纷、劳动纠纷、环境污染纠纷等。此种纠纷往往是在工业化、市场化、城镇化的过程中,农业、农民、农村的利益所面临的与非农群体之间的利益之争。这种纠纷已经超出了农村固有的系统,在纠纷形态上甚至带有某种“移植”的味道,在农村尤其是相对闭塞的农村它缺乏其相应的文化和知识基础,因此在发生之后常常让某些农村纠纷解决主体感到手足无措,陌生的对手、陌生的内容、陌生的形式,在没有外力的支持下,这种巨大的陌生感足以迫使一个茫然的农村纠纷解决主体选择逃避、隐忍甚至退却。因此在纠纷解决方式的选择问题上,将农村纠纷解决主体本身的境况与具体纠纷解决需要的文化和知识进行对应是一个必须要考虑的因素。
对农村解纷现状的把握,就是为了全面了解农村纠纷解决主体在解纷渠道选择上的具体做法,从中发现一些规律。按照通说的观点,纠纷解决机制大致可以分为私力救济、社会救济和公力救济三大类型,在不同的情境下,他们对应的解决主体有区别也有重合。
(一)纠纷主体本身。这种情形是指当事人认定权利遭受侵害,在没有第三方以中立名义介入纠纷解决的情形下,不通过国家机关和法定程序,而依靠自身或其社会力量,解决纠纷,实现权利。在这种情况下,纠纷主体本身就是当然的解纷主体。
(二)亲戚朋友。在纠纷主体感觉自身力量不足的情况下,向其社会网络中具有相应实力的人寻求支持就是必然的。亲戚朋友既可以作为支持一方纠纷主体参与到纠纷解决当中充当私力救济的主体,同时又可以作为纠纷双方所共同信任的中立方参与到纠纷解决当中充当社会救济的主体。
(三)宗族力量。在涉及到与外族人群之间的纠纷时(尤其是那些与宗族荣辱有一定关联的纠纷),纠纷主体很有可能会寻求宗族力量的支持。因为在这种情境下,相应的社会救济和公力救济力量相对不足,人们渴望通过建立某种可供借助的社会力量以强化其私力救济达到保护其权益的目的。
(四)村委会。在涉及本村人与外村人之间的纠纷时,村干部有时会充当起保护人,出面帮助本村村民解决纠纷。与此同时,在村民委员会下设置了人民调解委员会,它作为村委会专设的纠纷调解组织,是一种法定的社会救济主体。
(五)乡镇司法所。它是县(区)司法行政机关在农村乡镇人民政府的派出机构,承担着最基层政权组织的司法行政管理职能。具体表现为:协助基层政府开展依法治理和依法行政;指导管理人民调解工作;指导管理基层法律服务工作;组织开展普法宣传和法制教育;组织落实对刑释解教人员的帮教和过渡性安置工作;代表基层政府处理疑难民间纠纷。
(六)乡镇人民政府。乡镇一级政府作为国家基层的政权组织,承担着日常的行政管理职能,其中自然包括调处纠纷,维持稳定的基本任务。在乡镇中,常规的承担纠纷调处职能的部门主要是综治办,每个乡镇政府都设置了专门的社会综合治理办公室,简称综治办,负责把脉本地区的矛盾纠纷,力争在萌芽状态解决问题。
民事纠纷的类型影响着解纷主体的选择,进而决定着路径的不同。首先,婚姻家庭纠纷和邻里纠纷的主体大部分都倾向于选择村组以内的私力救济和社会救济主体来解决自己的纠纷。其次,赔偿纠纷的主体要么选择私力救济主体,要么选择公力救济主体。这种选择的原因在于相对于前两种纠纷来说,赔偿纠纷的主体重视的是自己的损失是否能够得到及时地弥补,因此解纷主体是否具有一定的强制力是他们选择的关键。再次,丧葬纠纷的主体总是倾向于用私力救济的方式来解决问题,只有在争端难以收场的的情况下才会勉强考虑接受村里的调解或其他方式。此外,宅基地纠纷、山林土地纠纷的主体一般倾向于通过正规的行政救济主体来解决。在这些纠纷中,纠纷主体意在主张权利和固定权利,而这些权利的客体作为稀缺性资源,又都处在国家行政权的管理和控制之下,因此在纠纷主体看来将纠纷直接交由行政权力来处理应当是最为有效的做法。最后,合同纠纷、环境污染纠纷、劳动纠纷中的农村主体则是希望通过行政力量来获得一定的辅助从而弥补自己在解纷过程中的信息不对称和实力不足。
当然,纠纷主体对解纷渠道的选择是一个众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在一个具体的纠纷当中,纠纷主体之间的力量对比关系、纠纷主体对纠纷利益的重视度、纠纷主体对相关法律的知晓度、纠纷主体对特定解纷主体的基本印象、纠纷主体之间的认知差异性、解纷成本的大小等都有可能影响纠纷主体对解纷主体的选择。
7月29日,中央在中南海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就当前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济工作听取各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详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