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6月,安徽某商贸公司(简称:“甲公司”)与上海某信息公司(简称:“乙公司”)在上海签订一份买卖合同,授权乙公司作为经销商在安徽某市经营某乳业公司(简称:“丙公司”)的产品,由丙公司进行发货,合同对于提货量,履约保证金等进行了明确约定。
合同签订后,甲公司向乙公司支付了履约保证金和货款,合同履行过程中乙公司提供部分货物后,以产品下架为由停止供货。2019年3月,甲公司通过EMS向乙公司发出《发货催促函》,催促其发货并告知合同解除事宜,该函件于2019年4月签收,后期交涉无果。
2019年3月—7月期间,甲公司老板多次带领数十名经销商来丙公司前台处,拉横幅“丙公司还我们血汗钱”,坐地不走,撕扯,发微信朋友圈毁损丙公司名声,持续数日,丙公司进行报警,经侦不立案处理,该聚众行为已经严重影响了丙公司的正常经营秩序,无法正常办公,且面临总部例行检查,开会等事宜,丙公司为息事宁人,无奈,非自愿的情况下出具的《垫付保证金声明》,同意代替乙公司垫付甲公司保证金和货款,并由丙公司加盖了公章和法定代表人签字确认。
2019年4月甲公司起诉乙公司和丙公司至上海宝山区法院诉求:一、解除2018年6月甲乙公司签订的买卖合同;二、返还合同履约保证金和剩余货款;三、赔偿实际损失和利息;四、丙公司针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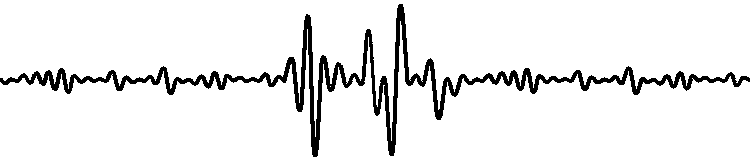
本所律师为本案丙公司诉讼代理人,本案为甲乙之间买卖合同纠纷,丙公司为产品品牌授权方和发货方,除产品质量问题,根据合同相对性,甲乙之间的买卖合同关系应当与丙公司无关,但丙公司出具了《垫付保证金说明》,不排除具有法律责任。
本律师接手此案之前,公司已经将《垫付保证金说明》交给了原告,以律师以往办案经验,如果公司同意垫付,并且法定代表人签字,公司盖章,根据法律规定,该行为不能对抗善意第三人,该案的争议焦点为丙公司是否有义务为甲乙公司之间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丙公司对外出具《垫付保证金说明》证据是否具备法律效力。
1、丙公司称自己处于无奈,非自愿,被胁迫出具的《垫付保证金说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规定,该《垫付保证金说明》为可撤销合同,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
2、胁迫需要具备以下特征:胁迫者有胁迫的故意,实施了胁迫行为,受胁迫者因胁迫而订立了合同,胁迫行为是非法的。
本案,表面上看,甲公司等人的行为确实符合上述胁迫要件,但证据取得非常艰难,本律师通过裁判文书网检索查询了大量案例,以胁迫为由,请求人民法院撤销,对证据的审查和要求极高,一般也难以支持,需要改变思路。
(1)法院认定公司法定代表人签字和公司盖章行为对外产生法律效力,本公司并未提供证据证明相对方知道或应当知道法定代表人行为超越了权限,相对方产生信赖,公司应承连带担保责任。(案号:2017最高法民申1475号)。
(2)法院认定根据《公司法》第十六条,对公司及股东的行为进行规范,属于内部治理规范范畴,不能以此为由约束交易相对人,相对人是否审查公司章程和股东会决议,均不影响公司对外应依法承担的民事责任。(2017最高法民申1696号)。
(3)法院认定公司为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担保的,必须通过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不属于效力性的强制性规定,判定公司对外担保有效。(2016最高法民申370号)。
(1)《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条:“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超越权限订立的合同,除相对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超越权限的以外,该代表行为有效”。
(2)《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六十条:“法定代表人以法人名义从事的民事活动,其法律后果由法人承受。法人章程或者法力机构对法定代表人代表权的限制,不得对抗善意相对人”。
(3)《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六条:“公司担保公司向其他企业投资或者为他人提供担保,依照公司章程的规定,由董事会或者股东会、股东大会决议;公司为公司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提供担保的,必须经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
3、2019年11月14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法〔2019〕254号)出台后,针对公司对外担保案件确立了统一的审理思路,法定代表人未经授权擅自为他人提供担保的,构成越权代表,同时根据债权人是否善意认定合同效力,并对善意标准进行明确规范。
本律师依据《九民纪要》最新规定,了解丙公司为法人全资100%控股公司,总公司作为股东并不知晓丙公司的对外担保和债务承担情况,法定代表人越权代表对外承担债务,公司章程也有关于对外举债或担保的由股东决定的规定,遂将一份《公司章程》作为重要的证据提交给法院,《九民纪要》打印版,提交给法官参考。庭审辩论中反复强调甲公司非善意相对人,并且没有审查丙公司股东决定。
根据2019年11月14日,最高人民法院《九民纪要》关于公司为他人提供担保第(17)规定:“公司对外担保不是法定代表人所能单独决定事项,必须以以公司股东(大)会、董事会等公司机关的决议作为授权的基础和来源,法定代表人未经授权擅自为他人提供担保,构成越权代表。”第(18)规定:“债权人主张担保合同有效,应当提供证据证明其在订立合同时对股东(大)会决议进行了审查,决议的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第16条的规定”。
原告并没有审查《垫付保证金说明》的来源和效力基础,不能被认定为善意相对人, 《垫付保证金说明》应为无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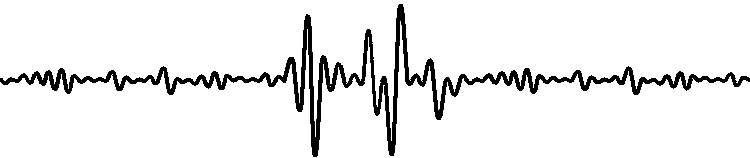
本案在上海宝山区法院历经四次审理,最终法院根据最新《九民纪要》规定,采纳代理人意见,认定丙公司出具的《垫付保证金说明》无效,丙公司不承担连带责任。甲乙公司解除合同,乙公司退还履约保证金,剩余货款和赔偿利息。但酌情丙公司应对乙公司对上述债务不能清偿部分的一半承担赔偿责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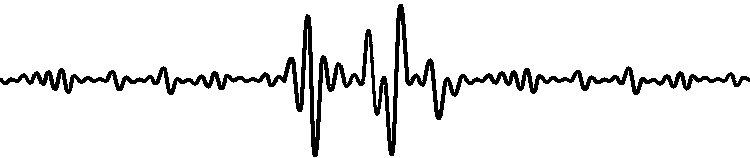
本案依据2019年11月14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法〔2019〕254号)关于公司为他人提供担保条款,对于同类案件的法律适用司法实践非常具备参考意义。该纪要对于审判实践统一了裁判思路,规范法官自由裁量权,增强同类型案件审判的公开性、透明度,提高了司法公信力。
2020年6月22日,上海宝山区人民法院作为典型案例发表其法院公众号,原创:马培,胡莎,胡明冬,名称为“宝山法院适用《九民纪要》认定公司对外债务加入无效 法官说案”,该案影响力较大,被新浪新闻、新民网、腾讯新闻,看点快报等各大网络转载,链接如下(可在浏览器中打开下述):
7.法院适用《九民纪要》认定一公司对外债务加入无效-闻蜂网 (360zimeiti.co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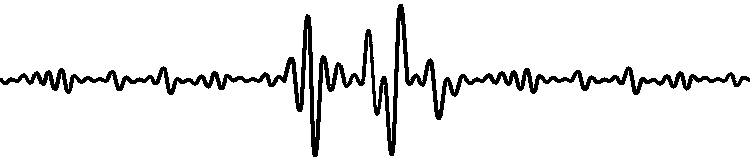
本案的委托时间为2019年10月18日,判决时间为2020年4月20日,2019年11月14日,最高人民法院《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法〔2019〕254号)的出台,明确规范了公司对外担保或债的加入和善意相对人的认定标准,统一了审判思路,公司对外担保或债务加入,法律实务界一直争论不休,为了减少“同案不同判”的现象出现,本案判决对于同类案件司法实践中的法律适用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本案认定《垫付保证金说明》无效,极力的保护了总公司和股东利益,降低供销企业下游经销商之间出现合同纠纷突破合同的相对性导致总公司连带责任风险。
考虑到债务加入的特点,准确理解和适用《九民纪要》确立的裁判规则,建议需要注意把握以下几个问题:
为防止法定代表人随意代表公司为他人提供担保给公司造成损失,损害中小股东利益,《公司法》第16条对法定代表人的代表权进行了限制。根据该条规定,担保行为不是法定代表人所能单独决定的事项,而必须以公司股东(大)会、董事会等公司机关的决议作为授权的基础和来源。法定代表人未经授权擅自为他人提供担保的,构成越权代表,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合同法》第50条关于法定代表人越权代表的规定,区分订立合同时债权人是否善意分别认定合同效力:债权人善意的,合同有效;反之,合同无效。
《公司法》第16条明确规定必须由股东(大)会决议,未经股东(大)会决议,构成越权代表。在此情况下,债权人主张担保合同有效,应当提供证据证明其在订立合同时对股东(大)会决议进行了审查,决议的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第16条的规定,即在排除被担保股东表决权的情况下,该项表决由出席会议的其他股东所持表决权的过半数通过,签字人员也符合公司章程的规定。
根据《公司法》第16条的规定,此时由公司章程规定是由董事会决议还是股东(大)会决议。无论章程是否对决议机关作出规定,也无论章程规定决议机关为董事会还是股东(大)会,根据《民法总则》第61条第3款关于“法人章程或者法力机构对法定代表人代表权的限制,不得对抗善意相对人”的规定,只要债权人能够证明其在订立担保合同时对董事会决议或者股东(大)会决议进行了审查,同意决议的人数及签字人员符合公司章程的规定,就应当认定其构成善意,但公司能够证明债权人明知公司章程对决议机关有明确规定的除外。
债权人对公司机关决议内容的审查一般限于形式审查,只要求尽到必要的注意义务即可,标准不宜太过严苛。公司以机关决议系法定代表人伪造或者变造、决议程序违法、签章(名)不实、担保金额超过法定限额等事由抗辩债权人非善意的,人民法院一般不予支持。但是,公司有证据证明债权人明知决议系伪造或者变造的除外。
债权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没有公司机关决议,也应当认定担保合同符合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合同有效:
1、公司是以为他人提供担保为主营业务的担保公司,或者是开展保函业务的银行或者非银行金融机构;
2、担保合同无效,公司不承担担保责任,但法院可以按照担保法及有关司法解释关于担保无效的规定处理。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五条:“担保合同被确认无效后,债务人、担保人、债权人有过错的,应当根据其过错各自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主合同有效而担保合同无效,债权人无过错的,担保人与债务人对主合同债权人的经济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债权人、担保人有过错的,担保人承担民事责任的部分,不应超过债务人不能清偿部分的二分之一。”





